99.99%普通人不该从历史中消失
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共同构建的,因此99.99%的普通人不应该被遗忘,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,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构成了历史的丰富多彩,他们的贡献和付出,无论是战争、和平时期还是社会变革时期,都为历史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,我们应该铭记这些普通人的贡献和存在,以更全面、真实的方式呈现历史。
上《十三邀》,录《圆桌派》,每年参加大量讲座、学术活动,历史学家王笛在这样高强度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节奏之下,依然保持高产。
今年,他69岁,接连出了两部书。一是他的“茶馆百年史”第二卷《茶馆: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(1950—2000)》,终于出了简体字版;二是两卷本《中国记事(1912—1928)》,近900页的巨著。
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江说,王笛是“农耕型学者”,深耕细作,稳扎稳打,不激不随。新周刊《世界观》栏目与王笛关于历史观的讨论,就从他的农耕生活说起。
“你知道怎样种出一吨重的南瓜吗?”
历史学家王笛问我。大约5年前,我曾经在成都听他闲聊,说起他在美国家里种菜的趣事。现在,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答案。
“买点堆肥,然后盛一桶水,抓几把堆肥放入水里,还可以加入一些糖。再拿用来养鱼的氧气泵,放水桶里‘咕咚咕咚’输氧24小时。堆肥里的生长菌会和氧气、糖分发生作用,密集生长,24小时后,你就得到了最好的有机肥料。把它浇到植物根部、叶子和果实上,蔬果会长得非常好。按照这个方法,我种出来的丝瓜可以达到近1米长、手臂般粗,一根能吃好几天。”
当一个历史学家去学种菜,他也会用钻研历史的态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,去做大量的文献阅读与调研。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江曾经戏称,自己是游牧型学者,而王笛是农耕型学者。王笛谈到农事时,尽管访谈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,他仍然兴致盎然。
“我对植物如何生长非常感兴趣,也喜欢到大自然里边去,开一两小时车去钓鱼。”王笛给我展示了一张渔获照,照片中他提着一条巨大的鲈鱼——像人们印象中的钓鱼爱好者一样,和战利品合影留念。
种菜是有规律可循的,什么样的土壤、肥料、气候能够促进植物生长,都有科学的方法。“但历史没有规律,历史是一连串的偶然。”对王笛来说,这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——他不相信历史阶段论、历史决定论、历史周期率等种种试图从历史中提取规律的可能性,更是他个人在将近70年的人生里的一大感触。
在节目《十三邀》里,王笛与许知远在一个小茶馆里进行对谈。
如果王笛的人生往另一个方向发展,或者换成另一个生长环境,今天也许就没有历史学家王笛了。
小时候,王笛住在成都布后街,稍后搬到成都东门一带。过了东风大桥就是乡下的田野,他经常跑到那边去钓鱼、游泳。有一次,一个小伙伴在游泳时溺水身亡,那是王笛父亲同事的孩子。还有一次,王笛在攀爬成都古城墙时,上面掉落一块大砖头,几乎就要砸中他的脑袋。
在王笛家附近的梓潼桥,沿街开着各种店铺,包括茶铺、早餐铺、卤菜铺、杂货店、酱油店等。他常常拎着瓶子跑到梓潼桥打酱油,跟哥哥用6分钱合买一个卤兔头,一人吃半个,一路走一路吃,最后走到卖小人书的书铺上,站定了,津津有味地看漫画。同学叫他“茶客”,今天他已经不记得这个绰号的来历,仿佛有一种“命中注定”的因缘,牵引着他成为研究茶馆的历史学家。
上大学以前,王笛从未想过要研究历史,他的志愿是成为一名专业画家。在母亲的影响下,王笛从小就热爱画画。中学毕业后,他去了铁路局,先是在基建分局的砖瓦厂搬砖,干了差不多一年的重体力活。因为会画画,后来他被调到工会负责刷标语、画墙报,算是一份体面工作。如果没有参加高考,现在的王笛也许已经是铁路局的退休干部。
1977年,高考恢复,王笛准备报名考试,被父母劝住了。他们担心读书人再次遭遇“臭老九”的命运,认为还是铁路局的铁饭碗有保障。考试那天,王笛正在上海出差,看到参加考试的人们纷纷走进考场,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弃了。那个瞬间,王笛站在街头,下定决心,无论如何都要参加下一年的高考。
王笛本来想考中文系,他想着文学和美术更近,可能以后还有机会当画家。结果,他的历史考了最高分,被四川大学历史系录取。
王笛是四川大学历史系七八级毕业生。倒数第二排左起第11位为王笛。(图/受访者供图)
1979年年底的一天,王笛去上政治经济学的课。当时,这门课属于大课,77级、78级的100多个大学生一起上。课间休息时,老师把麦克风接上收音机,广播中传来一条响亮的消息,在教室里回荡——“邓小平同志即将于明年1月访美”。全班同学瞬间欢呼,掌声雷动。
1985年读完硕士后,王笛留校任教,在川大教了6年书。1991年,他赴美留学。
“如果没有去美国留学,你会成为一个研究微观史的历史学家吗?”我问王笛。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《跨出封闭的世界》完成于在川大读研期间,是他对1644年至1911年长江上游地区的社会进行长时段、整体性研究的成果,体大思精,与他后来为一个茶馆、一群袍哥写的微观史著作有明显不同。
“绝对不会。”王笛的回答很干脆,“如果不出去,我看不到、也不懂什么是微观史。”
到美国读博后,他慢慢打开了史学研究的视野。20世纪90年代,从新文化史中衍生的微观史,在欧美史学界颇为流行,出现了不少杰作。从《奶酪与蛆虫: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》《马丁·盖尔归来》《接生婆的故事:玛莎·巴拉德传》等微观史经典著作中,王笛看到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向,如同卡洛·金茨堡在《奶酪与蛆虫》的序言中所说:
“曾几何时,历史学家们大可以被扣上只想知道‘帝王丰功伟绩’的罪名,但今时今日,这显然已经不再是事实。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了那些被前人沉默略过、弃之不顾或全然无视的东西。”
因此,微观史首先是对传统的宏观史、帝王史的反思,但并非站在其对立面,而是对历史图景的重要补充。“我并不反对帝王史。帝王将相对历史有如此大的影响,当然要书写。问题在于,他们只占总人口的0.01%甚至更少,凭什么占据99.99%的历史篇幅?这极不公平。”王笛说,微观史必须关注99.99%的普通人,这些nobody(小人物)和anybody(普通人)才是历史的主体。
留美期间,王笛越来越多地想起家乡成都街头的小人物,尤其是街头巷尾的茶铺里,那些来来去去的茶客和忙忙碌碌的伙计。如何为他们撰写一部历史?完成《跨出封闭的世界》30多年后,当他再一次去研究一个大时代,书写1912年至1928年的中国,他会如何着手?
以下是王笛的回答。
普通人在历史上并非碌碌无为
《新周刊》:“茶馆百年史”第二卷简体字版出版,至此,你的“茶馆百年史”算是完成了。孙江教授对《茶馆》有相当高的评价,他改写了希罗多德《历史》的开头来概括《茶馆》的意义:“在这里发表出来的是川人王笛的研究成果,其目的在于保存成都茶馆的功业,为了不至于因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,为了使茶馆里发生的那些令人感叹的过往的痕迹不致失去光彩,特别是为了把它们盛衰的原因给记载下来。”回过头来看,研究茶馆最难的地方是什么?
王笛:刚开始时,我感到茶馆是无法进行学术研究的。在《跨出封闭的世界》里,关于茶馆的内容只有几页,没法写更多了。那时候,我不知道哪里有关于茶馆的资料,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。过去也有人写过茶馆,但不是作为历史来研究。大家都认为它是一种文化现象,很有趣,但这种现象究竟有什么意义,大家从未思考过。
不光是历史学家,普通人对茶馆的研究也不关心,因为人民对自己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空间是麻木的。中国人喜欢读大历史。从小到大,他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是把历史作为激励、调动民族情感的一种工具。二十四史都是大历史,而且是王朝的历史,按照朝代更替和皇帝纪元来编写,这是中国通史的基本结构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的书经常被质疑:你研究这些有什么意义?
在成都,历史上大大小小茶馆和茶铺,有过许许多多的“功能”:社交场所、同乡会、职介所、婚姻介绍所、剧场、露天电影院、旅店、皮包公司办公室等等,并提供掏耳朵、足疗、擦鞋、流动报摊、流动小吃摊等服务,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。图为今天成都铁像寺水街的茶馆,中间是戏楼。(图/图虫创意)
《新周刊》:你在“茶馆百年史”第一卷里写过,曾经幻想自己穿越到20世纪中叶的成都,告诉茶馆里的人,你要为他们写一部历史,结果却遭到他们的嘲笑。
王笛: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,在茶馆里喝茶无非就是混日子,碌碌无为,对社会没有贡献,哪里值得历史学家去进行研究呢?老百姓认为自己是渺小的、不值一提的,遇到不公不敢抗争,需要表达诉求时也不敢说出来,因为人微言轻,说了也没有用。我认为,这是错的,也是传统历史观所造成的结果。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尊严和权利,虽然在受教育程度、经济状况、对社会的贡献上,人和人有所不同,但人人都应该享有尊严和平等的权利。
我写过一本书,书名就叫《碌碌有为》。我想说,我不反对写帝王的历史、王朝的历史。帝王将相对历史的影响更大,当然要写。但是,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连0.01%都不到,为何占据了99.99%的历史篇幅?这极不公平。难道那些占99.99%的人口,就应该在历史上消失吗?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被历史铭记,但是,我们能否为普通人群体在历史上留下应该有的位置?
王笛写茶馆,也画茶馆。在《茶馆》《袍哥》《那间街角的茶铺》等作品里,王笛画了不少关于茶馆的插画。(图/王笛)
《新周刊》:中国是历史阅读大国,不少历史著作可以卖10万册、100万册,但这些历史类畅销书大部分讲的都是大历史。这一市场现状,对于一些历史写作者来说,可能也是一种压力。就算他们对微观史感兴趣,也不大敢写。
王笛:这个情况符合大多数人的历史观和阅读习惯。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应该算是历史类第一畅销书,这么多年销量超过千万册,写的也是帝王将相。
这里面有历史材料的原因。目前留下来的大多数史料,都是讲统治阶级的。如果你要写一个普通人的历史,写日常生活,首先要找到非常有吸引力的历史记载。其次,就算写出来了,你想告诉读者什么?大家为什么要看?
我们关心康、雍、乾这些皇帝,是因为从小就被告知,他们是伟大的帝王。那些畅销书和电视连续剧反反复复地讲他们“成功”的故事,所以大家都感兴趣。如果写小人物,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普通人,我们读得过来吗?所以,在这样一种阅读习惯之下,对我这样的想写普通人的历史写作者来说,当然面临相当大的挑战。
但是,自从《茶馆》《袍哥》出版之后,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历史中的普通人感兴趣了。近年来,我专门为大众写的非虚构作品,如《那间街角的茶铺》《消失的古城》等,都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。当然,这只是一个开始,还有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。
王笛的“茶馆百年史”第二卷《茶馆: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(1950—2000)》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历史没有规律
《新周刊》:你刚才谈到,读者不知道普通人的故事具有什么意义。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:我们长期以来书写历史、阅读历史,有一个核心目的是寻找历史规律。就像司马迁说的,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。但从普通人那里,很难找到这些规律。
王笛:在《历史的微声》这本书里,我专门花了相当大篇幅讨论历史有没有规律的问题。我认为,历史是一连串的偶然。所谓“规律”,就是像物理、数学定理一样,能找到一条公式,然后所有事情都会按这条公式去发展。历史不存在这样的恒定性和规律性。
过去人们所说的研究历史的意义,就在于找到历史的规律,要不就是为执政者提供统治的经验和教训。为什么说历史有规律,而且大家也相信这一说法?因为在大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下,很多细节特别是一些偶然的瞬间、不经意的选择被省略掉了,只剩下粗线条的历史阶段。历史已经过去了,大家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历史,似乎能找到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,那不过是后见之明,完全不能预测未来将发生什么。
历史没有规律。也就是说,我们做的任何一个选择,都必须慎之又慎,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,依照过去的轨迹,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向,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,就一定会成功。(有这种想法,)我们会不顾及国情以及当时国际、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条件,甚至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。比如我在《中国记事》里写第一次世界大战,中国参加协约国就是一种偶然。主要是出于美国的敦促,而“革命的”南方政府是反对的,当时也完全有可能出现中国不参加协约国的结果。
不仅是历史事件,个体的人生也是由很多种偶然造成的。如果我高考的时候,历史考的分不是最高的,我就不会报考历史系。那我这一辈子怎么过,肯定是另外的故事了。
2003年夏,王笛在大慈寺文博大茶园拍到的景象——几桌顾客一边喝茶,一边打麻将。(图/王笛)
《新周刊》:寻找规律是很多历史学家的内在冲动,像唐德刚那样有个性的学者,也提出过“历史三峡论”,用穿越三峡来比喻历史进程的曲折,最后当然是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如果说历史没有规律,那么,作为一个研究历史者,我们要研究和寻找的是什么?
王笛: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。相比于寻找规律,我认为对历史的反思更为重要,尤其要对人类历史上的错误、不太光明的一面进行深刻反思。
我经常觉得,历史学家过分强调了自己的作用。从司马迁和司马光开始,我们就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非常之重。因为我们希望在历史里面找到规律,去告诉统治者应该如何治理天下。
实际上,二十四史都是胜利者的书写,是梁启超说的“二十四姓之家谱”。它能告诉我们什么?它隐藏和篡改了多少东西?在过去,朝廷修的历史才叫“历史”,民间学者的记载只是“野史”,是不被认可的。秦始皇为了统一自己的历史叙述,烧了多少书籍?乾隆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又毁了多少书籍?《四库全书》最终收录典籍3500多种,共3.6万册,但纂修过程中销毁典籍3000余种、15万册。
即便二十四史被写出来了,但是我们今天摸着心坎想一想,历朝历代有多少统治者正确使用过这些历史?有多少帝王和大人物真的会吸取历史教训,为民众谋福祉?据说黑格尔说过一句话: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,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。虽然我不能确认他是否说过这样的话,但未尝没有道理。
真正让百姓过上一点安稳日子的君主,往往都是因为他们“无为”而治。鲁迅先生在《灯下漫谈》里有一句话说得深刻:过去中国只有两个时代,一是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”,二是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。
如果说历史有规律,生活在秦皇汉武那样的伟大帝王的治下,普通老百姓几乎都过着悲惨的生活,这才是规律。当“伟大的”帝王要去创造历史的时候,就是人民颠沛流离、血流成河的时候。
我认为,对于普通人来说,如果我们相信历史规律,认为未来是按照某种规律向前发展的,实际上就停止了独立的思考,停止了对未来的探索,把命运交到被视为可以实现这些规律的人的手中。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,最好放弃发现历史规律、写出整体历史的雄心壮志,历史是个体的,是复杂的,是丰富多彩的,又是变幻莫测的。
李约瑟在成都拍到的一个露天茶馆,摄于1943年至1946年。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授权使用。
有血有肉的细节,让历史鲜活起来
《新周刊》:《中国记事》跟你30多年前写的《跨出封闭的世界》,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和关怀:大时代下的一个区域、一群人,如何走出封闭的世界?但这一次你的视角不再是宏观的,而是微观的,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和许多被遗忘的历史细节,让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晰了。
作者:访客本文地址:https://www.shaoshai.com/baike/1303.html发布于 2025-10-17 15:05:09
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打鱼晒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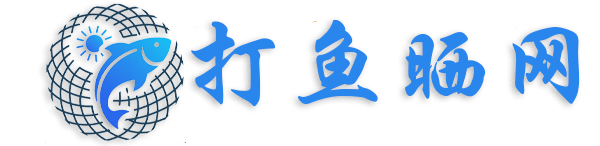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